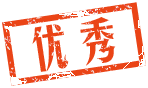我的爷爷
爷爷总说,他的童年是踩着哥嫂的影子长大的。三岁那年,父母相继离世,漫天黄土卷走了他的依靠,是比他年长许多的哥哥嫂子,把他搂进怀里,用粗布衣裳裹住了往后的寒暖。那时家里穷,嫂子煮的粥永远是稀得能照见人影,却总把碗底仅有的几粒米拨给他;哥哥下地干活,再累也会背着他走过田埂,怕他摔在泥里。那些年,日子苦得像嚼着生涩的野菜,但哥嫂的呵护,是苦里藏着的一丝甜,让他在颠沛里攒下了活下去的底气。
十七岁的爷爷,还是个眉眼青涩的少年,却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经人说合,他娶了十五岁的奶奶,一个梳着两条麻花辫,说话还带着怯生生语气的姑娘。没有像样的聘礼,没有热闹的仪式,就着一盏煤油灯,两个半大的孩子,从此成了彼此的家人。
最初的日子,满是酸涩与慌张。爷爷要学耕地、学织布,奶奶要学洗衣、学做饭,两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,常常手足无措。有一年冬天,大雪封了门,家里的粮食见了底,奶奶抱着冻得发红的手偷偷抹泪,爷爷攥着她的手,哑着嗓子说:“别怕,我去山里套兔子,总能让你吃上热饭。”他在雪地里蹲了整整一天,冻得膝盖僵硬,终于套回一只小野兔,炖成的汤,两人你推我让,汤里的鲜,成了那段艰难岁月里最难忘的滋味。
生活的苦,像磨盘一样碾着他们。爷爷曾为了多挣几个工分,顶着烈日在砖窑场干重活,肩膀磨破了皮,渗出血印,回家却笑着对奶奶说“不累”;奶奶也曾在夜里缝补衣裳到三更,眼睛熬得通红,只为给爷爷添一件能抵御风寒的补丁衣裳。可他们从不说苦,只是把彼此的牵挂,融进一碗热粥、一件暖衣里。爷爷会在赶集时,省下几分钱给奶奶买一块水果糖,看着她含在嘴里笑眯了眼;奶奶会在爷爷晚归时,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,等着他进门的脚步声。
日子慢慢熬着,酸苦渐渐淡了,甜香愈发浓郁。他们生儿育女,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,家里的土屋换成了砖房,稀粥变成了白饭。爷爷的背渐渐驼了,奶奶的头发也染了霜,但两人还是习惯了彼此的陪伴。清晨一起去菜园浇地,傍晚并肩坐在门口晒太阳,爷爷剥一颗花生递给奶奶,奶奶替他拂去衣角的灰尘,不说情话,却处处都是温情。
如今再听爷爷讲起过往,他总说:“这辈子,苦过涩过,可幸好有你奶奶,还有哥嫂的恩情。”那些酸辣苦咸的岁月,就像一壶陈年老酒,初尝辛辣,回味却满是醇厚。原来最动人的幸福,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,而是在风雨里互相搀扶,把苦涩熬成甘甜,让平凡的烟火,暖透了岁岁年年。